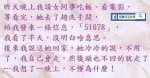4/4
下一頁
他的死是明朝最大的悲劇

4/4
▲于謙。圖源:影視劇照
于謙的死期果然到了。
重登帝位的朱祁鎮,內心被復仇情緒填滿了,似乎只有把舊帳清算完畢才能對他六年多的幽禁生活有個交代。而首當其衝,便是朱祁鈺倚重的「救時宰相」于謙。
奪門之變後第二天,正月十八日,于謙被捕下獄,罪名是莫須有的「意欲迎立外藩」——想要另立儲君。
正月十九日,朱祁鎮命三司九卿從速審理此案。
正月二十日,20多名官員在大理寺對於謙進行會審。于謙身遭酷刑,始終保持沉默。
正月二十一日,于謙被殺。
從立案到處死於謙,前後僅用了3天時間。這種非常規的死刑執行模式,表明有人迫不及待要于謙死。
根據史書的說法,朱祁鎮對於是否處死於謙還頗為猶豫,認為「于謙實有功於大明」,但徐有貞在一旁進讒言說:「不殺于謙,此舉為無名。」意思是,不殺掉于謙的話,你現在的皇位就是得之不正,沒有合法性。於是「帝意遂決」,下旨處斬了于謙。
處死於謙的同一天,朱祁鎮下詔赦免天下,並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。幾天後,被軟禁起來的景泰帝朱祁鈺,被廢為郕王。
朱祁鎮在詔書中,指責朱祁鈺當年是篡位上台,還對他8年來的為人、為政進行了全面的否定,大罵朱祁鈺「不孝不悌,不仁不義,穢德彰聞,神人共怒」,甚至詛咒朱祁鈺「既絕其子,又殃其身」。
經過朱祁鎮的抹殺,曾經堅決抗擊瓦剌、延續明朝國祚的朱祁鈺、于謙君臣二人,一個被黑成了「神人共怒」的昏君暴君,一個則被黑成了包藏禍心的奸臣野心家。
大約在奪門之變一個月後,朱祁鈺死了,年僅30歲。《明英宗實錄》說朱祁鈺是病死的,但這可能是朱祁鎮出於掩蓋真相而指使史官所寫的。野史的說法則是,朱祁鈺死於朱祁鎮派出的太監的縊殺。
朱祁鈺死後,朱祁鎮給他定了一個惡諡——「戾王」。隨後,又命人毀掉了朱祁鈺生前為自己營建的壽陵,另在北京西郊將他草草下葬。
明朝諸帝中,只有兩個皇帝不能進入皇陵,一個是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朱允炆,另一個正是景泰帝朱祁鈺。而這兩人身後命運的背後,是明朝立國不足百年間發生的兩起震驚天下的宮廷政變。皇權的爭奪,從來就是這麼赤裸裸,親情與血緣算什麼。
相對而言,朱祁鎮的手段比撿到皇位的朱祁鈺要狠得多。朱祁鎮或許僅有一個想法:我只是拿回原本屬於我的東西,只有他人虧欠我,我誰也不虧欠。
這種「不虧欠」的心理,也是人性使然。即便貴為皇帝,他亦無法超脫作為人的局限性。
就像作為臣子,石亨、徐有貞等人提著腦袋也要往上爬一樣。人總是以自我私利去指導自己的行動。畢竟世界上如于謙者,百年難得一見。
在奪門之變成功後,那些信奉富貴險中求的亡命之徒,一個個封官進爵。我也懶得一一去記述他們得到了什麼。我們只需要記住,他們也不是最終的贏家,他們僅僅淪為了皇權更替的工具。
這些人最終都迎來了不好的結局——在明英宗朱祁鎮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後,當年的奪門功臣一個個變成了亂臣賊子——石亨、曹吉祥等人均以謀逆罪被下獄或誅殺,儘管石亨謀反案可能僅是朱祁鎮羅織的一起冤獄;而徐有貞在政爭落敗後一度遭流放,始終得不到他想要的功名富貴,據說獲釋歸鄉後,每次酒後就繞屋一圈一圈地跑,邊跑邊叫「人不知我」,大概已經是瘋了……
從某種意義上說,他們跟于謙一樣,都是皇權之爭的犧牲品。只是,他們死得沒有意義,而于謙以高貴的人格,死後成了我們民族和國家共同膜拜的悲情英雄。
站在歷史的長河之中,當我們感受著流水的方向,就會發現任何宮廷政變其實也都毫無意義——除了增加陰謀與權術的運作,以教壞世人之外,根本沒有改變河流的方向。奪門之變更是如此。
我壓根兒不關心朱祁鎮與朱祁鈺兄弟的生死,抑或奪門功臣們的命運,他們要麼咎由自取,要麼死不足惜。他們都想掌控權力的開關,卻無一例外都是權力的奴隸而不自知。正如詩人所說,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。僅此而已。
而我之所以願意用這麼長的篇幅寫下這場毫無意義的帝國政變,僅僅因為它造成了于謙被殺的悲劇,從而印證了詩人的下一行詩句: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。
整個事件中,無數的人物來來往往,但經過歷史的淘洗,唯有于謙的遭遇和精神超越了時代。那個擁有權力而最終棄用權力的悲情英雄,或許是唯一有靈魂的人。是他,讓這段歷史值得被反覆追憶,被永久銘記。
于謙的死期果然到了。
重登帝位的朱祁鎮,內心被復仇情緒填滿了,似乎只有把舊帳清算完畢才能對他六年多的幽禁生活有個交代。而首當其衝,便是朱祁鈺倚重的「救時宰相」于謙。
奪門之變後第二天,正月十八日,于謙被捕下獄,罪名是莫須有的「意欲迎立外藩」——想要另立儲君。
正月十九日,朱祁鎮命三司九卿從速審理此案。
正月二十日,20多名官員在大理寺對於謙進行會審。于謙身遭酷刑,始終保持沉默。
正月二十一日,于謙被殺。
從立案到處死於謙,前後僅用了3天時間。這種非常規的死刑執行模式,表明有人迫不及待要于謙死。
根據史書的說法,朱祁鎮對於是否處死於謙還頗為猶豫,認為「于謙實有功於大明」,但徐有貞在一旁進讒言說:「不殺于謙,此舉為無名。」意思是,不殺掉于謙的話,你現在的皇位就是得之不正,沒有合法性。於是「帝意遂決」,下旨處斬了于謙。
處死於謙的同一天,朱祁鎮下詔赦免天下,並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。幾天後,被軟禁起來的景泰帝朱祁鈺,被廢為郕王。
朱祁鎮在詔書中,指責朱祁鈺當年是篡位上台,還對他8年來的為人、為政進行了全面的否定,大罵朱祁鈺「不孝不悌,不仁不義,穢德彰聞,神人共怒」,甚至詛咒朱祁鈺「既絕其子,又殃其身」。
經過朱祁鎮的抹殺,曾經堅決抗擊瓦剌、延續明朝國祚的朱祁鈺、于謙君臣二人,一個被黑成了「神人共怒」的昏君暴君,一個則被黑成了包藏禍心的奸臣野心家。
大約在奪門之變一個月後,朱祁鈺死了,年僅30歲。《明英宗實錄》說朱祁鈺是病死的,但這可能是朱祁鎮出於掩蓋真相而指使史官所寫的。野史的說法則是,朱祁鈺死於朱祁鎮派出的太監的縊殺。
朱祁鈺死後,朱祁鎮給他定了一個惡諡——「戾王」。隨後,又命人毀掉了朱祁鈺生前為自己營建的壽陵,另在北京西郊將他草草下葬。
明朝諸帝中,只有兩個皇帝不能進入皇陵,一個是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朱允炆,另一個正是景泰帝朱祁鈺。而這兩人身後命運的背後,是明朝立國不足百年間發生的兩起震驚天下的宮廷政變。皇權的爭奪,從來就是這麼赤裸裸,親情與血緣算什麼。
相對而言,朱祁鎮的手段比撿到皇位的朱祁鈺要狠得多。朱祁鎮或許僅有一個想法:我只是拿回原本屬於我的東西,只有他人虧欠我,我誰也不虧欠。
這種「不虧欠」的心理,也是人性使然。即便貴為皇帝,他亦無法超脫作為人的局限性。
就像作為臣子,石亨、徐有貞等人提著腦袋也要往上爬一樣。人總是以自我私利去指導自己的行動。畢竟世界上如于謙者,百年難得一見。
在奪門之變成功後,那些信奉富貴險中求的亡命之徒,一個個封官進爵。我也懶得一一去記述他們得到了什麼。我們只需要記住,他們也不是最終的贏家,他們僅僅淪為了皇權更替的工具。
這些人最終都迎來了不好的結局——在明英宗朱祁鎮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後,當年的奪門功臣一個個變成了亂臣賊子——石亨、曹吉祥等人均以謀逆罪被下獄或誅殺,儘管石亨謀反案可能僅是朱祁鎮羅織的一起冤獄;而徐有貞在政爭落敗後一度遭流放,始終得不到他想要的功名富貴,據說獲釋歸鄉後,每次酒後就繞屋一圈一圈地跑,邊跑邊叫「人不知我」,大概已經是瘋了……
從某種意義上說,他們跟于謙一樣,都是皇權之爭的犧牲品。只是,他們死得沒有意義,而于謙以高貴的人格,死後成了我們民族和國家共同膜拜的悲情英雄。
站在歷史的長河之中,當我們感受著流水的方向,就會發現任何宮廷政變其實也都毫無意義——除了增加陰謀與權術的運作,以教壞世人之外,根本沒有改變河流的方向。奪門之變更是如此。
我壓根兒不關心朱祁鎮與朱祁鈺兄弟的生死,抑或奪門功臣們的命運,他們要麼咎由自取,要麼死不足惜。他們都想掌控權力的開關,卻無一例外都是權力的奴隸而不自知。正如詩人所說,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。僅此而已。
而我之所以願意用這麼長的篇幅寫下這場毫無意義的帝國政變,僅僅因為它造成了于謙被殺的悲劇,從而印證了詩人的下一行詩句: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。
整個事件中,無數的人物來來往往,但經過歷史的淘洗,唯有于謙的遭遇和精神超越了時代。那個擁有權力而最終棄用權力的悲情英雄,或許是唯一有靈魂的人。是他,讓這段歷史值得被反覆追憶,被永久銘記。
 奚芝厚 • 311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311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9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12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12K次觀看 福寶寶 • 52K次觀看
福寶寶 • 52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5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5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6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6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5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3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3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3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3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3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2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2K次觀看